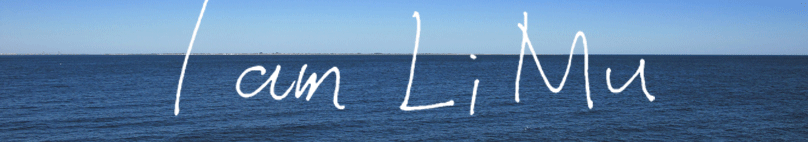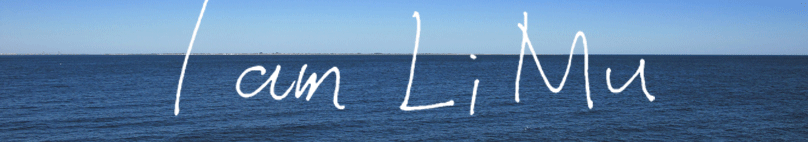|
| 【2009.12.19李牧和比利安娜的对话】 | Date :2011-09-05 | From :limu.cn |
| ------------------------------------------------------------------------------------------------------------------ |
![]()
LM:我们今天谈什么?
BC:谈你吧。
LM:谈我?有没有一个大的范围?
BC:你别这么紧张。
LM:我有点紧张的,因为我很少接受访谈。
BC:为什么很少接受访谈呢?
LM:我拍别人挺自在的,但是别人用摄像机拍我,我会觉得不自在,不习惯。
BC:你什么时候搬到上海的?
LM:2006年底。
BC:为什么?
LM:两个原因:第一个面上的原因是希望自己能有更多的时间去做艺术;第二个原因是在我教学的时候,突然感觉自己特别空洞,这种空洞让你觉得必须离开这儿,换一个环境重新开始一些东西,不然的话,你在那个环境里面可能一直会空洞下去。
BC:你在苏州呆了多少年?
LM:我是1991年考上苏州工艺美校,在那儿读了四年中专,毕业之后工作了两年。1997年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读书,毕业之后就回到苏州,当了六年的老师。一共在苏州12年。
BC:为什么当时选择了苏州?
LM:一个情结:想当老师。
BC:你在北京从1997年呆到哪一年?
LM:2001年。
BC:你是不是有一段时间跟一些做摇滚的人在一起?
LM:其实刚开始是背着一把吉他去北京的,因为知道北京有特别好的摇滚音乐。
BC:好浪漫。呵呵。
LM:到了北京的之后遇到一个弹吉他弹得特别棒的人,他叫小河,听他弹了之后,我觉得我不想弹吉他了。因为如果你想弹好吉他,可能要把你所有的时间、精力都用在这个上面。当时我意识到我的志向不在这里,所以从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就不弹了.
BC:那时还画画吗?
LM:那个时候画了很多画。
BC:那些作品都放在哪里了?我们都没看过的。
LM: 在老家有一些,自己手上还有一些。
BC:之后是什么时候停止画画的?
LM:停止画画应该是2003年的时候。
BC:为什么停止画画呢?
LM:在苏州当老师的那段时间里,看到好的画就令我激动,我当时画了一些画,我很少拿出来给别人看,可能在北京的时候看了很多泼皮或者波普的东西,还是挺受那些东西的影响的。当时觉得这些画也是在表达自己,但是,是不是真实的自己,今天还是值得怀疑的。2003年我觉得我画不下去了,原因是自己觉得画的没有意思了,可是我也没有新的想法。那时在苏州看到顾振清策划的“海市蜃楼”,在展览上看到很多上海艺术家的装置,还有影像。
BC:这个展览是在哪一年发生的?
LM:2002年,好像是冬天。当时我特别迷恋记录片。我课余的时间总是喜欢买一些记录片看。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我都特别喜欢。手里有个摄像机,自己也尝试着拍了一段记录片,当时画画也就放下了。
BC:当时拍了几个记录片?
LM:拍了两个内容,第一个内容是在回老家徐州丰县农村里,那里基督教特别盛行,村民们有很多很破的房子,都是教堂,周一,周三,周五都是聚会、唱诗。那里的基督教和城市里面的基督教还是很不一样的,它非常农民化,把基督当做一个神去看,而且是去求东西,比如说,我家的牛找不到了,我可以去祷告求基督,然后牛就可以回来了。但是我的条件不允许长期住在那里,我的工作是在苏州,而我的老家却在距离一千多里路的地方,你不可能把工作丢掉去做那个事情,所以只是拍了个半成品。
BC:那最后没有编辑?
LM:没有编辑,十八小时的素材放在我家里,用塑料袋扎着,从来没给人看过。
BC:还有另一个记录片呢?
LM:我在苏州的街上遇到一个留着长头发的中年男子在吹笛,吹得特别好。吹的是《姑苏行》,特别好听,听起来觉得很专业,我就拿着摄像机跟着拍。他带了一个徒弟,和一个女人,住在桥洞旁边的一个即将拆除的房子里面,他们给我讲他们老家的事情,怎么出来卖艺的。他们在苏州待一段时间后,转眼就要再换一个地方了,所以我从苏州拍到昆山,我有课的时候,我就回到苏州上课,当上完课我再回去找他们的时候,发现人已经没了,找不到了。一个月后,他给我打电话说他在杭州,我说:“我去杭州找你。”他说:“我们马上就要走了。可能要去广州。”那我就没法跟了。我意识到这样一个记录片我很难拍下去,因为我不能始终跟着他,于是这个记录片也就不了了之了。
BC:你那段时间在拍这两个记录片的时候还在画画吗?
LM:没画。当时苏州有我,赵罡,刘兵,还有陆明辉…我们几个人在一起玩,然后我就找他们,我说我们一起做展览,当时找的是戈多美术馆,老板是孙厚义,找他去聊,他还挺感兴趣的,“我支持你们,但是只是要你们出钱做本画册,画册很重要”。我说没问题,出多少钱我们都做。可能一本画册也就两万块钱吧,每个人摊钱下来也就是五千多块钱。后来“非典”来了,这个事情就搁置下来,之后他也就不再谈这个事情了。我们就自己找了一个朋友的公司,公司里面有个大厅,很适合做展览,就做了一个四人展览。展览的名字叫“逆向行走”,在我的简历上我有写这个展览。他们几个人的作品都是画,我展了第一个录像装置。
BC:当时做了什么录像装置?
LM:我分别拍了十个基督徒对着我的摄像机祷告的录像,把它放在十个电视里播放,电视机是做成竖着一排,横着一排,组成一个十字架的形状。
BC:你再回头看这个作品的时候,是如何看呢?
LM:我觉得它还是挺有力量的一个作品。这里面有一个张芳(我的太太)的祷告,这个祷告在最前面的那个电视机里,刚一开始很平静,然后就开始鼻涕眼泪往下流,我觉得还是挺感人的。
BC:她是基督教徒吗?
LM:当时没有受洗。她一直觉得他没有资格受洗,她坚持信基督教,但是她坚持不去受洗。这个作品在形式上并没有太新的东西,包括十字架这些东西,但是这是我非常努力并花力气做了一个装置,现场气氛也很好。
BC:那个时候还经常往上海跑吗?
LM:很少。
BC:那段时间你在做那个装置之后还有做东西吗?就是说不是为了参加展览,而是自己有做其他的东西吗?
LM:恩,拍照片,拍一些胶片的黑白照片,在苏州拍的一些废墟之类的,那时候苏州正在拆房子,去拍一些废墟里的沙发,拍了很多废墟里面别人丢弃的东西,比如洋娃娃,就是类似于那样的东西,然后回来以后自己手工上色。
BC:这个也没有展过?
LM:恩,没有拿出来过。
2004年春天,苏文祥在南京策划的“下一站”展览上,我拿了两个作品,一个是“忏悔”,拿到南京又重新做了一遍,当时我觉得希望更多的人看到,就又做了一遍。另外我又做了一件作品,就是把我用过的安全套全部装置在镜框里面,大概有四五十个吧,可能还要多一些,装裱在小镜框里面,然后把它挂了一排,每个安全套下面有日期和签名,像画一样的装在框里,然后给这个作品起的名字叫“幸福日记”。
BC:这个感觉更像李牧的作品。但跟你现在做的有点不一样。
LM:有点不一样吗?可能当时不像现在这么清晰地呈现自己的生活,当时还是比较注重一种形式感。但是有一个概念就是做艺术要大胆一点,要狠一点。
BC:你是2006年搬到上海的吗?
LM:是2006年底搬过来的。
BC:为什么没有去北京?
LM:来上海之前,我帮北京尤伦斯基金会拍一个记录片,上海的艺术家基本上都走了一遍,当时的采访对我来说是有很多感触的。之前我觉得这些艺术家都是挺牛逼的,是挺厉害的一群人。但是接触之后你会觉得每个人其实都挺好的,很亲切,很平和,讲话也很诚恳。我喜欢这种状态。
BC:那一次做采访,你是第一次接触这些人吗?
LM:第一次接触。
BC:那你以前交流过的人,还有谁呢?
LM:苏文祥,罗晓冬,李小松,在上海跟其他人没有太多交流。当这么几个人混在一起之后,你有一种归属感在这儿。我的家在苏州,还可以经常回去,照顾一下家里。
BC:那我个人觉得你2006年刚到上海,你还是比较隔离,我知道你以前也就是参加多伦的几个展览,证大的几个展览,就形成了另一个也不是圈子,但是在整个上海还是有一个隔离的群体,你觉得呢?
LM:其实当时就是跟小苏他们最好的朋友,我也是保持着一定距离的。
BC:为什么呢?
LM:我也不知道具体原因,我有一种本能,我觉得要保持一种独立的东西。我不太喜欢所有人吃喝拉撒的都混在一起的感觉,我觉得那种感觉会让我找不到自己,我希望我是独立的,但是我又可以和朋友们想见面的时候就见面,所以说我住在浦西的最西头儿了。我刚从学校出来,我需要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封闭的空间来自省,这个期间我需要读书,我觉得很多该读的书我都没读,我需要时间;我需要整理自己之前的好多东西和想法,希望能有一个新的开始。
后来李小松离开上海,到苏州去当老师了,留在这边的一个就是李原,苏文祥,罗晓冬我们几个在一起玩。再后来李原回武汉了,苏文祥去北京了,罗晓冬也去了北京。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想和更多的人交流,在心理上有这种愿望。很自然的就认识了你,认识小高他们,一切都是很自然的就过来了,也没有刻意地想要去接触谁。
BC:2006年的那段时间,你可能是花了一年的时间去看书,把前面做的事情做了一个总结,整理一下以前做过的东西,就是有一个新的开始,能不能谈一下你整理自己东西的一个过程,因为我觉得你在那段时间还是发生了一点变化,而且这个变化影响到你今天所做的东西,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转折点吧?
LM:从2006年底一直到2007年的后半年,在这期间,我读现代和当代的艺术史,然后读一些福柯的哲学。看艺术史很重要,要知道前人做了什么,而我又在哪里。在这个期间做的作品非常少,画了很多方案。茫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事,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愿望就是不想重复过去的东西,希望能突破一些条条框框的东西,但是自己真正做什么,自己是不知道的。几乎有半年的时间没做任何新作品,当时心里挺急的,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做了一个似乎找到了一点点感觉的作品。在上海城市里面的时候,每天坐地铁,你能感觉到人的一种紧张和焦虑,后来是用一组照片来表达的。就是把整个人垂下来,倒挂下来,把头发和衣服收起来,掩饰掉倒挂的痕迹,因为倒挂,脸部就会紧张,导致充血,一种很焦虑的表情,最后拍出来的照片被旋转180度,变成一张正常的照片。这个焦虑的感觉是我在上海能够感觉到的这个城市带给人的某种东西,当时试着去表达了这么一种东西,今天回头看这个作品,觉得和之前的作品并没有一个太大的不一样或者转变。
BC:你觉得是什么时候开始有了一个转变?
LM: “刷新”是小苏说要在证大做年轻人的展览,希望我能出一些方案,因为我和他关系很好,可能要求也比较严一些,出了几个方案,都被枪毙了。最后的时候出了一个“长城的风”的装置作品,那是很偶然的回苏州的时候,在旧货市场看到很多地方还放着那种长城电扇,这个长城电扇是八九十年代中国很火的一个国营企业,当时也是远销全世界的一个企业,但是后来这个电扇厂就再也没有动静了,我就有点兴趣,就是这个电扇是不是可以……突然感觉这个旧电扇身上承载着某些东西,至于是什么我当时说不清,我就跟小苏说:“我感觉在这个东西上面承载着一些东西,可以来做作品。”小苏说:“挺好,你往下想。”后来我就开始回去找长城电扇厂,当然现在那些厂房还在,都已经租给别人做写字楼、办公室了。找到他们当年的的销售经理,讲当年的销售情况,以及这个厂是怎么没倒闭的。后来我就决定拿电扇来做一个作品,我想收集当年的很多长城电扇,希望把这些电扇展现在展厅里,对着观众来吹风。当时我不想加其他的东西,觉得这个东西本身就可以说话了,有这种想法,于是当时就做了这样一个作品。对我来讲,这个作品突然打开了一扇门,之前我总是过于关注自己的身体,包括我的忍耐、所受的伤害。在这个作品之后,突然可以离开我的身体,用另外一个东西去说话,因为历史或者因为它的经历,它本身承载的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表达的。这个东西看似是一个电扇,可是它身上承载着一些民族的东西,历史的东西,我可以去表述,当时我觉得打开了这样一个口子。那个作品做完的时候,很多人都说看不太懂,包括杨福东看到作品的时候,他跟我讲:“这个媒介选的特别好,这个电扇本身素材特别有意思,但是你的作品少了一个转换,如果可以转换成一下,那么这个作品会更好。”我想他讲的也有道理,可是如何转换,当时我觉得我没有更好的方式,我能做的就是把这个东西呈现出来,把它当年的广告语和它的纸箱子呈现出来,甚至我想找到它当年在中央电视台上播放的那些每天大家都特熟悉的那些狂轰乱炸的广告,因为资料已经没有了,只能呈现这些,到今天为止我觉得也只能做成这样,而且我没觉得这件作品还有更好的转换方式。
BC:你最近两年做的一些作品,我觉得和这个电风扇还是很不一样的,虽然你刚才说的你以前是很关注身体、受伤害、暴力,可能这个电风扇的作品你是从这个系统里出来了,也可能你近两年做的更热忱的东西回到一个你和别人,这个世界,或者对方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关系里面,有吗?
LM:恩,有的。长城电扇这个作品,当时做完我并不是很清楚这个作品有多少价值,苏文祥跟我讲,他觉得这个作品里面有一种东西,一种很大气的气质,这个作品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作品。我开始读阿瑟.丹托的《艺术的终结之后》以及《普通物品的转换》,我想去了解一个日常中的生活物品是如何变成一件艺术品的。
2008年初,我做了一个录像,“行者”。那时候我经常会去人民广场,因为没有工作,就有很多空余的时间,我会坐在那里发呆,看着黑压压的人群,会有特别多的感触,但是这些感触是什么?如何表达?当时就有了这样一种念头,在人流中逆行。自己的生存状挺逆的,不是那么顺,然后这个行动似乎可以表达自己的一种状态。于是就有了“行者”那件作品。后来在我家给你看过的那个作品。
BC:我知道。因为我觉得你后面的那些东西很难去……比如说我对你后面的东西觉得还是有你自己的一个系统出现的这样一个状况,它可能跟日常生活非常紧密,所以也可以不是艺术,也可以是艺术,我对你这个东西觉得是很有价值的,很有趣的一个东西,比如说你前面说的那些作品,包括那个“行者”,因为我上次也跟你讲了,我觉得你就是拍了一个录像,但是也做了一个行为,做了一个录像的记录,当时你坐在那边看那个人群的感受未必用这个方式表达是最恰当的,所以我觉得你的很多作品,是存在一个很大的挑战,你这些细腻的感受怎么去展现出来和怎么去表达?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很日常的,把它变成我们所谓的艺术在展厅里面可能会显得有点虚假,所以要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这个感觉怎么去保留,但是又可以把他展现出来。就比如说你做的“左手日记”,包括赤脚走路,都是很日常感受的东西,而且有一点很有趣的东西是消磨时间的,也可以说是很可怕。我觉得你最近两年的转变就在这些地方,似乎有一个你的对生活、对生命的很特殊的一个感受的出现。
LM:我一直都不太敢把这个东西呈现出来的,其实这就是是艺术。今天去看昨天的东西,你会觉得可以再大胆一些,但是当时总希望把它变成一个可以展示的录像。你说的那个感觉到城市的冰冷,赤脚去行走,去消磨时间,我一直不太敢把这个作为艺术呈现出来,我觉得这只是我的生活,我想去做这个事情,我只是在试着找感觉,而不是说这就是艺术,当时是这种状态。
BC:我只是觉得你的这个“非艺术”和“是艺术”,我自己觉得是比较有趣的一个东西。可能你最近几年做过几个没有拿出来展过的,但是一直在做的东西,它也跟你的生活贴得很近,也不是为一个展览做的,我个人看待,你对艺术的一个比较明确的态度,或者没有态度,总之就出现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比较有趣的东西,是你的一个气质。
GMY:听了一会,觉得李牧和很多做艺术的人很像,就是一开始他在找什么是艺术,什么是大家心中都认可的一种艺术,所以他会说他刚开始做的十字架的电视,心里感觉好像抓住了艺术就是这样的,但是看了他后来的一些作品,发现他其实慢慢地又回到了自己的一个状态,比如说他一直没有展出过的“礼物”,或者“左手日记”,我觉得这个就是慢慢地他更在做自己的艺术了,我想知道一点,你做自己艺术的同时,你还有应付那么多展览,就是说你怎么在展览的命题下跟自己的艺术找到一个权衡的方法,这是艺术家都面临的问题,你是怎么去权衡的?
LM: 以前参加展览,我觉得用“应付”这个词比较准确,到后来我觉得用“应付”这个词对我来讲不太准确了。之前我觉得很累,参加一个展览,报了很多方案被枪毙后再报,弄的自己很不舒服,但是往后就不再为展览而做方案了。当有展览来的时候,不管是什么样的展览,把你自己呈现出来就可以了。不管展览是什么样的命题,你卖作品也好,探讨经济也好,探讨政治也好,我是怎么想的,那我说出来就可以了,我不需要考虑其他太多的东西,我明白这一点之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不太难了。
GMY: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你怎么呈现你的东西呢?想是很重要的一步,是一个观念,怎么呈现出来的东西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有不同的形式,跟更新的形式组合在一起呈现出一种新的形式,现在艺术越来越多的是用不同的方式组合,那你自己觉得你现在有一个方案出来后是一个习惯性的思路去呈现东西呢还是会尝试一些不同的方法呢?
LM: 我找一种能最恰当表达我的方式,最恰当的表达就是最好的,不是说我要找一个和别人不同的或者说是要突破什么的。当你的想法产生的时候,怎么去表达,你会有很多选择,选择里面最贴近自己的,我觉得就是最好的。
BC:我一直觉得你这些东西展现是有点儿难度的,就是找一个很恰当的方式。
LM:恩,我知道它的难度在哪里,难度不是像一个录像或者照片那样贴出来而已,因为我后来做的作品,我能把我做的作品和我的生活联系起来,就像我每个月月底要去少管所上课一样,我要想一些办法跟孩子们交流。它展示难度就在于如何把自己的体验让观众也能体验到,而不是告诉观众你做了什么,这也是和我之前做的作品有很大差距的地方。
BC:你现在的“左手日记”还在做吗?
LM:在做。最初我没有把它当作品去做,只是想试一试写写是什么样子的,感受一下,写一段时间觉得特别难继续,因为就是一个手,后面一个环境,没有太多变化,手上不可能写太多的东西,画一个图形,或者写一句话。我就觉得这对我是一种训练,训练自己如何把这一天或者某一刻刹那间的感受,在手掌上用一句话一个词表达出来。这是一个我很主动愿意去训练自己的一个方式。
BC:那你每天做的话,你怎么选时刻把这一天的东西写下来呢?
LM:随机。第一个是有了空闲的时间;第二个觉得我该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有很多时候白天事情太多了,一直拖到夜里,为了完成作业,赶快去写,很仓促的拍一张。很有闲情的时候,有时间了你可以很精心的去选择构图和写什么东西。
BC:有没写的时候吗?
LM:有时候连着两天没写,因为我实在找不到感觉,或者是忘了。
GMY:关于这个我有一个问题,你说怎么把当天的感觉表达出来,就是说准确的感受着力点是在(因为最后呈现是在照片)整张画面,还是在手心,亦或者在上面的字?
LM: 所有的因素。你放置手的时候,背景是什么,手的姿势是什么,手上的内容,所有的东西,尽可能希望能准确一些。
BC:你昨天写了吗?
LM:写了。因为昨天阳光快要落下去的时候,马上就要没了,我就把手伸到一个阳光的影子里面,手上写了“每天的阳光总是那么短暂”。
BC:我看了你的博客,其实我很少上别人的博客,关于你奶奶去世那天,你就回老家之前写了一段文字让我很感动。
LM:那是“best wish for you”。那天是我奶奶去世了,我要赶在我回家之前(因为我第二天要回老家奔丧),把“礼物”寄掉。认真的去选购礼物,寄完之后,开始写那天的“左手日记”,我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不管任何时候都是Best wish for you,希望把最好的给你,然后就写在手上,拍了那张照片,当时觉得这样能表达我的感受。
BC:你那个“礼物”作品还在做吗?
LM:在做。
BC:还是同样的人吗?
LM:对,一直是一个人,这个月寄完了就可以了。
BC:你每个月给他寄一份?
LM:对,每个月寄一份。这个月我想寄一棵圣诞树。
BC:寄了吗?
LM:没有,我跑了很多地方,还没找到一颗自己最喜欢的圣诞树。
BC:我在文章中提到过,“左手日记”里的的背景也可以说是随机的,但是你在做这个的时候有一个时间和地点的选择性,有意思的是它永远不让这个东西变成一个很具体的东西。所以你只能猜测时间和地点,这是他的有趣之处。你讲讲你的那个“礼物”吧。
LM: “礼物”是基于前面几个作品的基础上才做出来的。
BC:哪几个作品呢?
LM:我前面这些作品,都是一个一个扣着来的,比如说我做那个在电梯上行走的作品,尽管这个作品是一个行为,它会让我意识到你和周围的行走的人之间的某种联系。之后做的“公共知识”,把自己家里的书搬到展厅让观众借走。那时候在上海呆了一年多的时间,没有工作了,其实挺愿意把自己打开,和更多的人交流。方案拿出来之后遭到很多人的批判,很大家都觉得没意思。当时你给了我很大的肯定,你说这个想法不错,可以去做。
BC:我不记得。
LM:那天晚上我挺有感触的,因为李平虎他们有点不负责任的乱讲我的东西,有点发泄,后来我晚上在自己的日记上说有些人只图自己嘴上的快感,而不考虑别人是怎么想的,只会从形式上去判断别人的东西是好是坏,事实上这是一种挺自私的方式,因为别人任何的一个想法,你要考虑别人背后是怎么想的,而不是仅仅是它呈现出一个什么东西,这样的去批评别人,是不负责任的。但是我觉得你对我的肯定是挺重要的,我意识到似乎有些东西在里面,这个东西特别不像艺术,但是我又觉得对我个人来讲又比较有兴趣,我想去做这个事情。我就是说,任何一个方案出来,自己都不能确定,所以你周围的朋友的鼓励,会让你沿着这个方向往下思考。如果在它刚产生的时候,像个幼苗一样,一巴掌就被拍死,那它永远都不可能长得强壮起来。
BC:是的。
LM:说到这个,我觉得“蓝色图书”就更不像一个作品了,甚至我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真的是不把它当作品来做的,就是有点像公益活动,可以说没有一点艺术的痕迹在里面。做这个作品的过程里面我会去思考艺术到底是什么东西,结果是即使弄清楚艺术是什么也毫无意义,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好了,只要我觉得对自己重要、有意思。是不是艺术一点也不重要。
这时候在街上捡了一张名片,因为我不是去选择的,是很随机的遇到这样一个人,那我就很随机的把一些最好的东西,一些祝福去送给他。这个随机性是我很感兴趣的一个地方,就产生了这样“礼物”。这个作品会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礼物很难选,因为我根本就不了解对方。
BC:是吗?
LM: 刚开始有点艰难,甚至有一个月,我跑了无数的礼品店,拿下放下,拿下放下,人家会不会喜欢?!买这个东西对他有没有意思,这个东西有没有价值?大概做了几个月的时候,我突然明白我不是给对方寄礼物,我其实是在给我自己寄礼物。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觉得不难了,寄礼物也不难了。就是你认为是最好的东西就可以了,这个作品越往后面做就越顺。
GMY:做完之后,你想去认识他吗?
LM:不想。东西越不具体,就越能有想象力。
BC:有一定的距离。
LM:对,距离产生美,这个想象会让在我心里面留下美好的东西。
BC:我认为你在建立一个跟外界或者跟别人的交流,你似乎在每个作品中建立特定的游戏规则,还是保持着一个距离,虽然你把你的书拿出来给别人,别人也可以还你,或者跟你产生关系并交流,包括这个寄礼物,其实都是在你的一个特定的游戏规则里面产生的交流,其实很还是一个有距离,你可以控制整个局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想过。
LM:这是我的性格,我和所有人都这样,除了我最爱的人,其他人都保持着距离。我觉得距离对于别人是一种尊重。就像我刚来上海的时候,我都没有和朋友吃喝拉撒住到一起去,我需要这种距离,包括我和你,和小高,我们关系都非常好,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保持着一个距离。我之前经历过很多次当距离太近的时候可能会伤害别人的事情。
BC:你怕别人伤害你还是你伤害别人?
LM:别人也会伤害我,我也会伤害别人。我和我的父亲以前会发生很多冲突,父亲会对我说很多很难听的话,让我很受伤害,而他却不去伤害他的朋友和邻居,那是因为我们俩走的太近了。而且我这个人如果和别人走的太近,我说话会口无遮拦,会挑最重的话说出来,会伤害到别人。我会有意识地和所有人都保持着距离,但是这不妨碍我和大家的关系,更不妨碍我希望能对大家好一点。
GMY:李牧很真诚,我觉得你的艺术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你越来越在靠近自己做一个比较真诚的东西。
LM:前几天我和一个以前的大学同学MSN聊天,他说:“我很信任你,因为你从来不会撒谎。”我说:“你说的对,我是一个不会撒谎的人,我想撒谎,可是我不会撒谎,但是今天和以前有一点不同,今天是即使我会撒谎,我也不愿意去撒谎。”
BC:恩。胡昀,你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HY:你前面说到长城电扇的那个作品,我没看过,我觉得长城电扇这个作品很不像是你做的一个作品,而且你刚有说你至今都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解决方式,因为我觉得这个完全不是你的工作方式,所以我就觉得你说是它把你打开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作品和你的关系不是很大。
BC:我们可能现在看这个作品跟李牧也没关系,但是这个作品对他自己可能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就换了一个工作和思考的方式,我们觉得从李牧的一个大的宇宙看待,未必是很重要的,但是对他自己我觉得很重要。
LM:你老在一个房子里呆着,有一天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契机把你从房子里带出去,走出去看了一下,也许后来你还是会回到这个房子里来,但是当你再回到自己这儿来的时候,你对你自己的认识就不一样了。我以前总是想把艺术抱的很紧,因为我来上海,我要执着的做艺术,但是朦朦胧胧的让我感觉到没有艺术,只有生活。张芳一直跟我讲,不管你做什么,你做的快乐才是第一位的。这句话对我帮助很大,如果不快乐,它可能不是我喜欢的事。不管我做的好,做的坏,艺术本来不存在,没有艺术。只要我能做的快乐,做的高兴,那就是最圆满的事情。
12月19日,上海
参与者:比利安娜、高铭研、李牧、胡昀
|
------------------------------------------------------------------------------------------------------------------
© iamlimu.org 201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