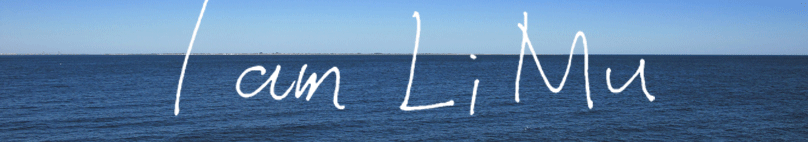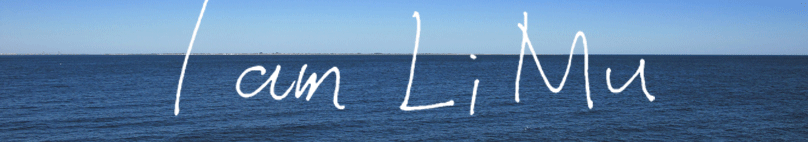|
| 对话 李牧/王辛 | Date :2012-07-23 | From :iamlimu.org |
| ------------------------------------------------------------------------------------------------------------------ |
![]()

李牧(LM):我之前看过几篇你写的文章,都是英文的。我知道你的中文也很好,可是你却选择用英文来写。你觉得它们之间有什么差别?
王辛(WX):我用英文来写评论是因为整个大学里面思维和写作的训练都是用英文进行的。它不只是一个选词的问题,更是一个遣词造句和文章组织的感觉。长期用英语写作之后就会发现不太知道怎么样用中文来写这样的评论文章了。 这也跟一些专业词有关系,翻译过来很生硬,就直接用英文写了。用另外一种语言写作的时候,有种感觉你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语境里,因为语言是一个文化系统,即使一句话意思相似,感觉和表达却不同。
中文的艺术批评里面,你有没有觉得它有时很注重文字性,甚至有点文学性的在写,但是我觉得艺术批评应该是先讲清楚事情,可能你的文章写得特别美,但是别人却不知道你要评论的内容是什么。
LM:你是在说批评的客观性吗?
WX:我觉得说得简洁清楚是比较重要的。但是感觉很多时候读到一些艺术批评写作,一上来就用一个宏大的理论框架,然后再把这个展览套进去,然后再拐到另外一个东西上。这种实质上很格式化的当代艺术批评写作比比皆是。
LM:是的,国内很多评论给人的整体感觉像是绕口令一样,看不懂。他们把很简单的事情用晦涩的理论复杂化了,我一直觉得这样是不对的,这样的评论在艺术和企图了解艺术的人之间立起一堵墙。我觉得一个好批评家写的文章就应该像一个好艺术家做作品一样, 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表达复杂的现实。
WX:我倒觉得艺术家是可以晦涩一点的,因为艺术家不一定要把自己说的特别清楚,可以非常个人化。可是如果是写批评文章的话,那首先要让别人弄清楚所谈论的对象。中国的艺术批评可能受欧洲的影响大一些,在欧洲有些艺术批评非常哲学化,尽管写的跳东跳西,但是作者的思路很清晰,讲述也很严谨。很容易造成学的人只学了一个表皮,学不像。美国的教育则是强调一定要把话说清楚,因为作者很容易会沉醉进文字里面去。这个听起来很容易,但是做起来挺难的,比如我们读研究生的课时有这样一个很基本的小训练,就是教授会给你一张画来描述。有些人一上来就会说这幅画体现了什么什么,或者这体现了某个哲学流派,教授就说我只是让你说这幅画,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各种视觉元素是什么,如何相互作用,在这个基础上再去谈其他。
LM: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艺术评论并产生兴趣的?
WX:其实我对艺术评论本身的兴趣并不大,因为我还是觉得艺术,或者研究艺术更重要。艺术批评只是一个衍生品,所有和艺术相关的东西都是衍生品。艺术批评对艺术有用,可我不知道它本身有什么意义。
LM:你的高中是在哪里读的?
WX:在国内读的,高三一边准备高考一边申请学校和奖学金。我当时选择来美国读大学的原因是不必提前选专业,大三定专业,只要选够学分就可以了。而且鼓励广泛涉及不同学科。
LM:你不知道你会来美国学习艺术,是吗?
WX:不知道。我大二才开始上美术史课。可能因为特别喜欢这门专业,所以成绩特别好(笑)。后来就把它定为专业了。我还有另一个专业是数学,辅修心理学。
LM:在美术史课上都具体学习什么呢?
WX:本科基本上是通览:古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巴洛克、19世纪到现代主义、当代艺术的艺术史,艺术理论入门类课程,还有一门课是博物馆学,但我没赶上,亚洲艺术史方面分中国、日本和印度。
LM:学了三年之后,你是一种什么状态呢?
WX:你是问我那时候对美术史的看法,其实是挺难概括的。因为现在很难分辨某些特定的知识是什么时候获得的。本科读完后,脑子里确实是有一个美术史的框架,框架不等于美术史本身,但是会对思考有影响。
LM:你读完本科后就决定要读研究生吗?
WX:我读本科的时候做过一些实习,比如MoMA和在苏富比。在苏富比实习的时候帮助准备当年当代中国艺术的秋拍,那次拍卖也给了我从另一方面深入地了解中国当代艺术的机会。最初喜欢在拍卖行做,因为可以上手很多东西,可以细看很多原作。但是到后来我就发现它需要其他方面的头脑,竞争特别残酷,甚至有些不择手段的竞争。那一年正好又逢美国的经济危机。归根结底我更感兴趣的是研究,之所以对拍卖行感兴趣只是因为能更近距离的接触艺术品。我本来是想毕业后直接工作,而不是去读研究生,那时候会觉得自己对美术史已经有足够的了解了,现在看根本不是,因为还没有能力去深入进一个话题里去讲。当时我的老板就说你还是去申请研究生吧,现在的经济前景不乐观,你毕业后可能找不到工作。所以我就申请了研究生。(事实证明她的预测和建议都非常正确。)
LM:你为什么申请哥伦比亚大学的艺术史专业?
WX:当时就是想到纽约市来,而哥伦比亚和纽约大学的艺术史专业都非常强。例如在哥大任教的有October的创始人之一Rosalind Krauss, 她是现当代领域里很重要的评论家、美术史学家。我的导师Robert E. Harrist Jr.是研究早期中国艺术我极为尊敬的学者。就是因为有这些人才选择了哥大。而且在纽约工作机会也多。
LM:你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方向是什么?
WX:主要是东亚的传统艺术,但选其它课程也完全不受限制。中国方面包括早期书法,宋画,花鸟画史;日本艺术是狩野派,江户时代艺术史等;另外又修了印度美术史、文艺复兴、当代艺术理论方面的课;还有一门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讨论课。
LM:你为什么不直接选当代艺术来研究,而是选了传统的艺术?
WX: 第一,我觉得本科上完之后对这方面的了解还远不够,且大多数本科院校里并没有特别深入的东亚艺术研究,本科美术史通览也只是学到皮毛。其次是想能够与当代艺术维持一个距离。
LM:为什么?
WX:因为我觉得了解美术史还是很必要的,因为不断钻在当代这个尖上面反复讨论必然有局限性,而涉猎的领域越广,包括对艺术史(甚至艺术史之外的)了解更多的话,它能让你看某些问题看的更有意思一点,会有一些不同的视角。这就是为什么总能看到一些艺术家自己以为很先锋,但其实不然。一些研究传统艺术的学者也会对当代性有一些很值得深思的观点:比如高居翰教授(James Cahill) 在2005年有一篇小文章里提到过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即在文人画的语境里,后现代在元代就已经发生,元代到明代是文人画的后现代主义时期—如果按照后现代的一些基本理念,比如艺术为了艺术,讨论一些艺术本体论的问题,那元代的文人画已经在讨论这些问题,明代到清代更是变本加厉。
LM:刚才你说你的导师是个很好的导师,怎么好?
WX:我对他研究的方法及内容比较感兴趣,比如早期的中国书法。他有一本专著,写早期中国的摩崖石刻,叫“文字的风景”, 因为自然的山水和风景不是一回事,风景是是通过人的眼光和人的活动造就的,所以他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中国的摩崖石刻,比如说泰山上那些石刻,镇江焦山为死去仙鹤写的动人祷文《瘗鹤铭》等,研究这些书写的来龙去脉。他又不只是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研究,他还会引入古罗马废墟中文字的研究。
LM:你觉得他的研究比中国人研究的还要深入吗?或者说站在不同的位置?
WX:他站的位置不同,同时研究的也非常深入。很多中国的学者诟病西方对中国的研究,但我觉得重要的是看别人怎么样把一些新的视角带进来,包括一些平行上面的比较。
LM:我也思考过这些问题。在中国推动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舞台上的进程的多是外国人,我预感到他们尽管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但是他们有一个很致命的坎,第一是因为他们是用西方已经形成的标准、价值观来推广中国的当代艺术;第二,他们缺乏对中国人精神上的理解,甚至有些东西他们永远无法理解,这是中国特有的,甚至是和整个当代艺术体系不协调的东西。我想,能真正推动接下来的中国当代艺术的人应该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自己。目前在中国从事策展和评论工作的中国人大多不具备一个国际的视野,甚至是很狭隘的,这些人不能真正但当此责任。这样的人可能会出现在国外留学多年,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和知识,同时对中国的当代艺术感兴趣,又在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才能推动它。
WX:有道理。但是最终还是资本和意识形态在控制。好的人才和美好的愿望是推动艺术发展的重要的元素,但可惜不全如此。
LM:整个当代艺术系统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对东方文化的一种需要、好奇、或者误读,还包括政治上的一些因素,这构成了意识形态上的影响。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不是个体能把控的,那么你能做什么?做什么才能可能产生一个好的推动?
WX:在国外留学的人总是有个忧虑,觉得回国之后会很难适应,可能在最初的阶段会有一些摩擦。。
LM:我觉得这些最终都不会成为问题的,最终的问题是你想做什么。
WX:是。如果明确了自己想做什么,这些问题就都是浮云。
LM:前几年我还认为作艺术你能做的好坏取决于你的条件,包括你是否很有才华,是否有很多机会。这两年我认识到这些都不是问题,你能否作出好的艺术,能否成为一个好艺术家,完全取决于你想要什么,其实也就是你的理想,这个理想决定了你能走到哪里。
WX:我很同意理想的说法,我做这个选择其实也是很理想主义的,大多数本科或研究生过来读书的国际学生一般不会选择艺术史, 最初选这个专业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能做什么,甚至都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工作;但是你也会面对另外一个现实,就是在理想和你的能力之间的衡量,还有理想主义状态和真正要达到的目标以及你所做的努力之间也许存在一些误差。你永远不知道在这个努力当中你什么时候会偏开,偏离最初的想法。
LM:我觉得选择做艺术研究、评论,这和选择做艺术家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WX:对,因为总要面对行业内部的政治,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的政治,很多时候可控制的是比较少的,但不代表不能去做努力。
LM:你觉得那个力量很强大吗?
WX:我觉得你单纯这样问,不是在一个具体的事件中,很难回答。只能说有的时候是会让人比较无奈。
LM:你会经常遇到这样的无奈吗?
WX:我会经常看到这个行业自己为自己设下一些限制和障碍,不规范的小机构不谈,即使是纽约这些大型的机构,大都会,古根海姆,新美术馆,惠特尼,他们在按照既定议程推动艺术的同时也有自身的限制,包括他们给自己设定目标和执行之间的差别。
LM:落实在你自己身上,你遇到了哪些冲突和无奈?
WX:就有大有小吧,很难说。但是现在已经成了我的现实的一部分。
LM:你是指你在大都会博物馆工作所感受到的东西吗?
WX:我觉得大都会反而是给我很大的自由度的一个地方,而且那些我不熟悉,有待更深入了解的艺术领域会让人产生谦卑之感,有时也能帮助跳出自己研究领域的条框。我所说的更多是专注于一个方面的美术馆,比如说惠特尼是专门研究美国艺术的机构,一方面目标清晰,另一方面也是一种限制,它会造成一种短视。
LM:你说的这些都是你观察得来的,你是否想过,如果你进入这些机构工作,你是能改变一些东西的。
WX:能改变,也是有限度的吧。
LM: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一个人在他所处的环境中,他的角色是什么,他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他所处的环境?我就试着去做一些事情,看看是否能改变一些东西。
WX:我觉得做这些最大的意义是对你自己的,外界是不可控的。
LM:对,只有对自己有意义的时候,才能对外界产生意义。
WX:无论在当代艺术之内还是之外,都有一个问题是圈子化。有时候就是大家志同道合而形成的一个圈子,有时候是实际问题上的考虑。我接触到过许多不同的圈子,这里面还会更细分成很多小圈子,当代、传统艺术都如此,彼此之间交流很少,甚至壁垒很深,有时候让我很困惑。在外人看来,艺术已经是一个比较小的圈子,但是这个里面还有很多很平行的、之间几乎不来往的世界。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不能通过体制和一个框架来改变,你只能通过个人的兴趣来做一些什么。所以我和一个建筑师朋友也在做一个论坛,请年轻的一些emerging professionals一起分享讨论自己做的是什么,所在领域是什么,虽然大家觉得建筑和艺术是两个比较近的领域,但是建筑师和艺术史研究的人和艺术家面对的现实是特别不一样的。参与的有艺术家,独立策展人,建筑师,还有天体物理学的博士,也许这产生不了一个实际的效果,但是它能给每一个参与到的人一些新的启示。尽管没有直接的结果,但是也许知道十年、二十年之后会产生有意义的启示。
LM:做艺术和做建筑的人所面临的问题真的很不同吗?
WX:我指的是面临的具体职业现实很不一样。
LM:这让我想到Vito Acconci,他从一个艺术家转变为一个建筑设计师,很多人都觉得很可惜。其实我觉得他只是换了一个媒介而已,他做的还是相同的事情,他依然是一个艺术家。还有一个人是林璎,我们都知道她设计了越战纪念碑,她是个建筑师,可是她还活跃在艺术领域,她创作了很多艺术作品。所以我觉得艺术和建筑之间的差距并没有那么大,你可以选择走在他们之间的边缘上,你可以用艺术家的身份来作建筑设计,就像Vito Acconci;也可以用建筑设计的身份来作当代艺术,就像林璎那样。
WX:并不是说大家一定要跨界,而是说可以把思路稍微解放一点,因为有的时候越是对一个行业投入,就越容易陷入这个行业本身固有的一些细节里面。
LM: 我来到美国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看了很多展览,可是我总觉得我看到的都是产品,不是艺术,这种感触很强烈。似乎有一种艺术的标准,很多人依据这个标准来生产艺术。
WX:我觉得这已经都不是标准了,而是一种陈词滥调。这是一个问题,因为从来没听说过当代艺术一定要怎么样,它貌似最鼓励个性最怕趋同,但是为什么在哪里看的展览都大同小异呢?
LM:这背后一定是有一种类似标准的东西在起作用,谁都知道当代艺术是没有固定概念的,可是大家创作出来的东西都在暗合某种标准。这也包括我的作品,我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一直在努力的工作,希望我的作品能进入一个艺术的循环系统,这个系统就是我们去美术馆、艺术中心、画廊看到的那些东西,我变成了一个大的工厂体制下的一个生产者。我们按工厂的标准来生产,产品是艺术。当我意识到这个大的艺术体制的时候,我有一种本能,不想按这个大工厂的标准来生产,我想做另外的东西,寻找另外的可能性。这也是我为什么接下来会把我的工作室从上海转移到我的老家,一个农村里去的原因。我想换一个环境,人只有理想是不够的,如何实施它变的很重要,如果我的原料和机器都是大工厂提供的,那我就不可能生产出其他的产品,那么我可以改变我的原料,我也可以改变生产方式,更换机器。我已经意识到一种危险性,如果我一直这样住在纽约,从美术馆和画廊汲取营养,我必然会生产出这个标准之下的艺术。
WX:当代艺术一个很大的陷阱是,在它六十年代甚至更早发端的时候,它是反对现行的体制的,可到现在已经发展成连反对体制都变成非常体制化的行为。还有一个是反专业性,但是现在反专业性本身也成为一种专业性,就是你该怎么去反,针对什么去反。当代艺术发展到这个阶段已经跟传统的其他的时代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了。它主要还是受一些意识形态、资本和政治力量的推动,就比如说这些双年展,或者说这些独立空间,美术馆,你会意识到,现在的美术馆,藏家,策展人之类,和以前的教堂、教皇没有什么区别。那时候你就是按照根据教义的标准去做一些东西,现在只不过这个教义没有那么明确的阐释给你,但是大家还是在生产相似的东西,而且还要在这个体制里面做到最好。这个运行的机制可能在早年是不太一样的,最初反艺术、非艺术这些概念提出来的时候确实有划时代意义在其中,但是等这些东西被纳入体系之后,就又成为之前体制的变相延续, 甚至还更加变本加厉。因为它的规则都是不被阐明的,大家都要去猜,我应该做什么样的作品才符合当代艺术标准?我怎么才能被选入威尼斯双年展或Documenta?这就是为什么在大都会这样一个地方,虽然有大机构的官僚性,但是对我来说,你能时刻意识到还有这么多不同的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促成的艺术流派,它称为一个提示,而我觉得这种提示很有必要,很健康。
LM:当我来到纽约一个月后,我对这儿的艺术的感觉就是健康。我看了一些展览和活动,我觉得整个纽约的艺术氛围还是很健康的,这是和上海相比的结果。可是通过我们刚才的谈话,我觉得这个健康本身也是很值得质疑的。认识是很重要,做什么当然是更重要的。你对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是否有些计划和打算?
WX:如果我要告诉你我的理想是要做艺术家的话,你会怎么看?
LM:真的吗?你想做艺术家?
WX:我做过作品,大学时还做过个展。可能是基于对艺术的兴趣,想试试看作为不同的参与艺术的实践者,是什么感觉。
LM:就是说你现在还不确定你具体的工作方向?做策展人、评论家、研究者、或者艺术家?
WX:所以我现在都在尝试,除了做艺术。除了正职,我现还写些评论,完全不限于中国当代艺术,比如新美术馆三年展展评,或是大都会日本艺术展厅琳派特展。也写研究性的文章,比如馆藏的一套陈洪绶十九岁时画的册页。我现在知道怎么回答你的问题了,虽然我不知道我将来固定会去做什么,但希望依靠持续的知识储备和观察,现有工作带给我的自由,做一些不那么职业化,但是非常认真的事情。看看这样做下去能有什么结果,因为职业化的引力实在是太大了,像我在哥大的一些同学会直接去读博士,他们觉得那个是最正确的,当代艺术这一块则就觉得你应该去做策展人,最后做到某些大型展览的策展人,仿佛就是事业的高潮了,这都要求很高程度的职业化,我觉得还是可以试着在一个比较深入的程度上,在不同的领域进行一些研究和探讨,这个不是表面上的艺术家反职业化,反而会跟艺术和艺术史更贴近。但现在没有特别明确的想法。
LM:想法不明确也不是坏事啊,有时候它会带来新的可能性。
WX: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说,没有明确的想法也许是不好的。
LM:有创造性的工作往往都不是一开始就有一个明确的结果和目的的。
另外我觉得不管你将来做什么,都需要一个相对宽的认识上的视野,只要你对某项事情感兴趣,你只要认真的去做它,就能做好的。或许明年我来纽约的时候,会看到你的展览在某个艺术中心展出,那也是很令人激动的事情。
WX:我觉得有可能啊(笑)。
LM:你会有很多创作的想法吗?
WX:还比较多。我会特别敏感于美术史上有意思的关联,我会想把这个放进作品里面去。这可能会导致做的作品可能太美术史化了,基本上成了你对美术史的观点的一个注脚,但当作品成为一个注脚,作为作品本身存在的意义在哪里?许多观念艺术的桎梏也在这里。我大学的时候做了一些比较美术史波普的油画,回头看其实就是学生习作,做出来了,又觉得缺点什么。
LM:有时候我不得不说,创作的时候,知识成为一种障碍。
WX:对,但是你又不能没有知识。
LM:最起码在创作的时候是要忘掉知识的。
WX:那你怎么忘掉知识呢?我很好奇。
LM:进入你的身体内部最本能的,想做的东西里面去,就可以了。也就是不要用你所拥有的知识来做任何判断,或者控制它。我能做到,因为我没有多少知识,我对艺术史和哲学都是一知半解的,这些东西会启发我创作的动机,但是当我真正进入创作里的时候,只有我的心,我的本能来决定我怎么做。
WX:那要是一些潜意识里的知识在影响你,该怎么办?
LM:不管它。那是你左右不了的,就让它影响吧。
WX: 你规划自己的道路吗?
LM:从来不规划。
WX:所以你才有很多来自家庭的阻力,是吗?
LM:是,这个也是不能规划的。你不得不承认阻力就在那儿,不能回避。
WX:你想追求的事业和家人对你的期望之间的矛盾,以及紧张的关系,你现在是怎么处理的?
LM:刚开始压力挺大的,现在倒没什么了。当我深陷矛盾之中的时候,我被矛盾所困扰,那时不能站出来看自己。我通过我的作品让自己站出来看自己,换一个角度看自己,发现其实这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也是很小的问题,你参照整个大的环境,你就会问你能干什么,能妥协吗?不能。那就不要妥协,也就是不管它了。这不是放弃努力,而是切实的作点什么的开始。就像我的父母总是抱怨我离他们太远了,一年只能见一个星期,我不能关照他们。那好,我就想,如果我回到父母身边住两年,我还能做艺术吗? 他们抱怨我没有孩子, 我觉得需要一个合适的时间,不是因为要解决问题才要孩子。
WX:你这个解决方式挺完美的。就是一举多得。
LM:对于未来,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呢? 当我看到很多灾难性的事件时,就会把很多事情放下了。你假设自己是灾难里的一员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应该尽量在生活里面给自己减少一些遗留。谁也不知道那一刻何时来临,能做的就是尽量少的遗留给这个世界一些麻烦。
你对我的作品有什么建议吗?
WX:你在上海少管所做的那个《蓝色图书》达到一个很公益的效果,那你觉得它和一个公益项目有什么区别呢?通过公益来探讨艺术和把艺术作为社会公益还是不太一样的。
LM:我没有答案。 我也基本上不回答别人这个问题,我不想回答。 通过这个作品,观众可以看到很多信息,关于少管所,关于艺术家,关于年轻的犯人,关于监狱里的体制。艺术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再说,区分它是公益还是艺术,对我没有任何意义。
其实,对于我做过的作品,大多是不喜欢的。
WX:为什么会这样呢?
LM:因为我喜欢的作品总是下一个,还没有做的。在未来,而不在过去。
WX:是因为它没有完全表达你对艺术的理念吗?
LM: 我觉的我完成的大多数作品,离我想要到达的地方还很远,距离很大。
WX:你对你想要的东西能说出来吗?
LM:讲不出来,我只是知道那个东西将会更贴近我的生命,和艺术史、艺术系统以及任何文化价值观都没有关系。
WX:当我看你展示你的回到村子里的计划时,我当时特别乐的是你把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的行为录像放在小卖部里的小电视上展示,我觉得那可能是她的作品最有意思的展示环境吧。因为我对这个艺术家不是特别喜欢,尤其是最近美术馆对她的神化,从开幕式嘉宾到美术馆晚宴上的巨型(助兴)表演。MOMA回顾展要神化她的目的太过明显,而她自己也加入到这种力量里面去。她最近还开了一个阿布拉莫维奇表演/行为艺术保存中心,如果这个中心是广泛收藏行为艺术作品来讨论怎么样保存,呈现,和再现,那尽管可以批评她把表演艺术体制化,本质还是有意义的。但她把整个观看和参与的过程都规定下来了,所有的观众都要穿白大褂,要戴手套,就像进入医疗、科研机构一样,然后必须在里面呆两个小时,每一步体验都被严格限制,按照她设想的来体会,我觉得这就太超过了。而且还要打上自己名字的标签。前年在纽约大学听过她的演讲,个人感觉得她对艺术的理解完全像二十世纪初期的男性艺术家。但是你把她的作品放到那样一个农村小卖部的环境里去,我觉得比放在任何一个美术馆都好玩。
LM:我觉得她可能是太忙了,每天都是派对以及展览的邀请,哪有时间来思考艺术呢?
WX:但是她自己以为是在为行为艺术的推广而奔走。
LM:不,最好的推广是做出更好的作品,别人会替你去传播和推广。如果自己变成推广者,反而会浪费了思考艺术的时间。
2012年6月
纽约布鲁克林PointB屋顶花园
王辛, 做艺术史研究也策展,写研究型文章与艺评。现任纽约一艺术博物馆特展研究助理,不定期与朋友组织Gesamtkunstwerk 1020跨学科小论坛。
|
------------------------------------------------------------------------------------------------------------------
© iamlimu.org 201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