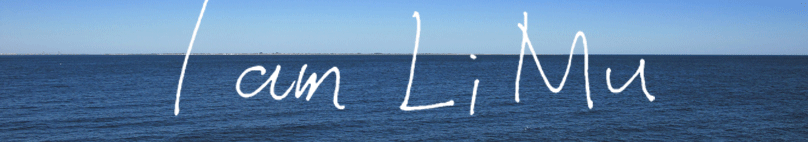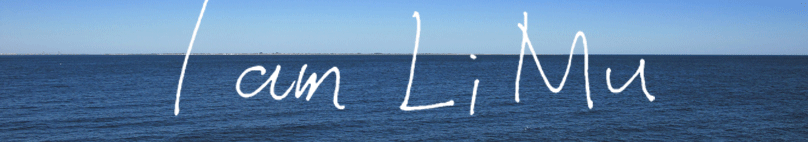|
| 对话:胡昀/陆平原/李牧 | Date :2012-09-04 | From :iamlimu.org |
| ------------------------------------------------------------------------------------------------------------------ |
![]()
(今天是2012年7月26日,PDF已经发行了5期。今天,PDF的三位负责人,李牧、胡昀和陆平原,从前5期PDF碰到的一些情况和问题展开,对接下来的工作提出一些想法并进一步讨论可能存在的变化。此外,李牧刚从纽约回到中国,所以谈话也涉及了一些关于李牧在纽约的生活,以及他的收获。)
胡昀(HY):我觉得你回来之后还不是特别适应,你要经历一个心理的变化。
李牧(LM):我今天下午去了M50,看到路边上的展览海报,还有开着门的工作室,以及正在布置的展览,我就觉得气场很不对,感到这儿乌烟瘴气,低俗趣味泛滥。这让我有一点不适,不过我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去强调这种不适感,而是要看到背后的原因,并且思考我应该怎样工作。
陆平原(LPY):纽约也有类似M50这样的地方,像切尔西,它也应该会有一些低俗趣味,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LM:在纽约有切尔西、下东城、苏荷、布什维克等很多画廊区和艺术家工作室聚集区,那边也有低俗趣味的艺术,我也会抱怨看不到多少好的艺术作品和特别好的展览,但是它给我的一个整体感觉是充满活力并且很健康。其实今天在全世界的当代艺术环境中也找不到多少特别好的艺术家,这是整个当代艺术的问题。但是我回到国内这个环境的时候,就是觉得这种低俗的趣味有些泛滥了,并且感觉不到多少生长中的活力。
LPY:因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还不到30年,整个步调可能是有些滞后,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HY:步调滞后是肯定的,我觉得它始终没有进入一个健康、良性的轨道,当然一切都是从没有到有,可是这边的问题是它走上一个歪路,包括这个行业中的很多部分,畸形发展,有点往死胡同里走,这是个比较大的问题。在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有点进入一个死胡同了,这是我的感受。对于李牧来说,之所以会有这样一个落差和不适,可能是你的心理变了,因为你的变化而导致你不适应这个环境。这个环境一直都是这样,我想知道你自己的变化过程。在这5个月的时间里,还是有一个过程的。你在上一期杂志里也写了17小段(《在纽约的17个段落》,李牧,PDF05期),多多少少提到一些影响到你的人和事,能不能具体说一下呢?
LM:五个月的时间有点长,我不知道该从何讲起了。
在去纽约之前,我并不是特别自信,因为我不知道自己的作品是好是坏。去了纽约之后,我在很多不同的场合介绍自己的作品,我觉得我获得了很大的信心,我觉得我能成为一个很好的艺术家,尽管我知道我离一个好艺术家还很远。这种自信在国内从来没有过,这些自信来自哪里?我在纽约的期间,我去看别人工作室里的作品,去美术馆看大师的作品,我能感觉到哪些作品离艺术很近,哪些作品离艺术很远。艺术是什么?我是用什么来判断这个远近的?作品是个桥梁,当作品对我的心灵产生撞击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这是件好作品,是无疑的,不需要其它的任何理由。艺术是很直观的东西,要靠我的本能去感受,不需要参照其它的资料,策展人的文章,其他人的评论,都不需要。这对我接下来的创作会有影响,我希望我能做出离艺术更近的作品,离我的心更近的作品。
HY:我记得你和谢德庆聊过之后,提到过艺术家不一定要做什么,就是艺术家可以不作为,这个想法是那个环境给你的吗?
LM:我说的艺术家不一定要做多少作品,是有一个针对性的,针对的是我们做的太多了。当时我说,艺术家谁也不欠,他不欠这个社会的,也不欠任何人的,那他所有的行为都应该是自发的,是他愿意做的。可是这个环境导致艺术家想要参加更多的展览,想要认识更多的策展人,想通过作品来获取更多的金钱,就不得不去做很多并不想做的事情。所以我说艺术家谁的也不欠,艺术家有感觉的时候可以做很多作品,没有感觉或者不想做的时候可以什么都不做。这个影响来自和谢德庆的会面,我很难用一两句话讲清楚我的感受,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我越来越感到他对我的重要性,因为我看到了我一直想要追求的一个艺术家的状态,我们平时也一直在讲什么是独立,可是我们却在做很多我们不想做的事情,或者说不得不去做的事情,我们都会无奈的说没办法。我看到了一个人,他从来不对自己说没办法,如果是他想做的,他就去做,不想做的,他就拒绝。他不依赖于任何人、机构和体制,他完全不依赖这些东西。我看到的不是一个做艺术的方法,而是一种人格。以前我会问我自己:你能做到这样吗?现在有一个人,他就是这么做的,而且做的这么好。那我就会觉得,其实我也可以做得到这样。
HY:在纽约你见了谢德庆、蔡国强、李明维等比较知名的艺术家,还有那颖禹,在国内并不是被人所熟悉的艺术家,这些谈话和交流是不是导致你心态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LM:是的,和人面对面的交流远远胜过我去美术馆所获得的经验。我之前对谢德庆的作品也非常了解, 同样,我也了解蔡国强的很多作品。但是当我看到人的时候,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当你看到有温度、呼吸着的一个人,和之前在图片上看到体验是完全不同的。就像我见到谢德庆第一面的时候,他的那种平和、亲切都会让我怀疑:那些作品是他做出来的吗?因为看图片的时候有个人的想象,你会把艺术家给神化了,只有见到他本人的时候才会觉得,他就是一个人,他跟你没什么差别,就是因为他去做了,所以他那些作品就在那儿了。如果你去做了,你的作品也会在那儿。这让我觉得做艺术其实很容易,很简单。如果你不接触他本人的话,你会把他神话,也会把艺术复杂化。和人直接见面的经验对我来说是特别重要的。
这次我在纽约最不积极的事情就是去美术馆和画廊,一个原因是我去年曾经去过这些地方,今年我就提不起兴趣去那里。另外我警惕去美术馆看展览会形成一种惯性,就是每过一段时间就要去美术馆和画廊去看,累得腰酸腿疼,其实并没有看到什么,却有一种充实感。我很警惕这个东西,我担心我会依赖那些东西。
LPY:你看到过印象深刻的展览吗?
LM:肯定会看到一些,有一些零星的作品和展览使我印象深刻。
我有几次和一群朋友一起去看展览,这些朋友中多是策展人、艺术家和写评论的,都是对当代艺术很熟悉的朋友,我发现大家看展览都不是很认真,会用自己的经验在展品上扫一眼,表面上没有看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就不会再去了解它了。一个很大的展览,我和朋友们大概的看一圈就出来了,接下来会用很长的时间来聊天,说这个展览是如何如何的没意思。但是没有人能很具体的说出某件作品为什么没有意思,总是很笼统的去谈论。那时候我意识到我看展览有些“油”了,如果用这种经验式的、居高临下的态度看展览的话,那我什么都看不见。之后我看展览的时候,尽可能的说服自己,要像第一次看展览一样,仔细的来看每一件作品,也许看不完,但是要保证很认真的看每一件出现再眼前的作品。看的时候不要去判断好和坏,看到它里面闪光的东西,不同的东西,这样的收获就会很多,就会看到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所以,当你问我看到哪些好东西的时候,那我就回答你,第一是好展览和好艺术家非常非常的少,甚至会很长时间都碰不到一个;第二,其实在每件作品里,无论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每个艺术家的工作室里,你都可以看到闪光的东西。
LPY:你对好作品的定义是什么?在你去纽约的前后有变化吗?
LM:我不太会用一个很清晰的标准去说,我更多是凭我的直觉。不管是在视觉上、心理上,还是在思维的观念上,如果它能启发我、打破我的固有经验,或者在情感上能感动我,我都觉得那是很好的作品。以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
LPY:你在纽约觉得这种好作品特别少,会不会跟语境有关系,在他们的语境下是往前走了一步的好东西,由于我们没有这种语境,所以会无法辨别作品的好坏?你觉得会有这种可能吗?
LM:没有。我觉得艺术是不依赖于语境的。所有的作品都是人做出来的,人无非就是探讨生命和他的环境,观念的束缚与开放,今天整个地球上的信息相对还是比较流通和开放的,艺术可以探讨另外一种文化和环境,而不依赖于那种文化和环境,你可以看不懂一本书,一篇学术文章,但是一个艺术作品应该是能看得懂的。(我回答的有些武断,其实我还是遇到很多一时难以理解的作品,我必须去阅读相关的文字去了解作品的背景,之后才能理解作品,这并不一定是不好的作品。)
HY:还有一个问题,你说那个环境给了你一个自信,是否这种自信是任何一个艺术家都能感受到,无论是什么样的艺术家,就是说当一个艺术家处在那样的环境中,他多多少少都会很自信,他会认为自己做的东西是有意思的,是否这个环境会造成这样一个结果?
LM:其他人我不知道,我只说我自己。我所获得的自信是基于对我过去所做的工作的认可,而不仅仅是来自别人对我的尊重和赞扬。
HY:这种认可是从比较中得到的吗?还是一个反馈,不一定是赞扬,哪怕是他愿意听你来介绍,无形中他会给你一个自信的感受。因为在这边很难找到一个人真正的耐心听你说什么。
LM:我的自信更多是来自比较。我会把我的艺术和别人的艺术去比较,特别是和同时代,同年龄段的艺术家去比较,我也会和美术馆里的作品去比较,我会知道我离他们有多远。你说的很多人到了美国获得自信,那不一定是在艺术上的自信,而是作为一个人活着最基本的自信。人在那样一种环境里很容易获得一种自信,来自人和人之间的尊重。
HY:我们有一些身边的例子,比如说有一些从事行为的艺术家,他也许生活在纽约那样的环境中,至少他自己很认可他做的东西,在我们看来有一些作品并不是那么的优秀,但你会感受到他有一个很强的动力,或者说他有一个很执着的心态,他就要这么做,他就坚信这个东西,你觉得这个和你谈到的自信是一样的吗?因为你说的比较也好,更多的标准是你自己的。你在用一个你认可的标准去判断,然后得出了你对之前自己的工作的认可。那同样这种认可可以存在于另外一个艺术家,他也有他的标准。他也会通过向别人介绍自己的作品,慢慢的形成这样的自信,在这样的气氛中,在这个环境中,是不是说每个艺术家他都可以认可自己的作品,是很优秀的,会很容易的产生这种自信。
LM:对,在纽约那个环境里面,你想听到别人批评你,说你的作品不好,那是很难的,这是基于一种礼貌和尊重。其实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里都不会一下就做的特别好,总是一步一步的做出来。那个环境里的这样一种尊重,形成了一个相对来讲还算是健康的一个成长环境。对创作者而言,他做的幼稚或者说不成熟,是被允许的。我觉得在国内的这个环境,不客观和不健康的批评声音过多。
HY:哪怕不是不健康,也是片面的,简单化的去归类。
LM:他并不真正关心你在想什么,而是看你的结果,像谁,是否和谁撞了车,是哪一类。这直接会影响艺术家的思维和心态。
LPY:我觉得对心态影响是比较大的。
LM:就像我的“蓝色图书”那件作品,我在国内展览和向别人介绍的时候,更多的人问我:这和一个公益活动的区别在哪里?或者会给我归类说这是公益类的艺术作品。还有人会问我的观念在哪里?同样的作品,我在纽约和芝加哥展示的时候,很多人会问我:你在这个作品里的体验是什么?在这个活动的前后你对少年犯的认识发生了什么改变?他们对你产生了什么影响?
HY:在某个层面上来说,艺术其实应该是针对人本身的,它不像科学、手工艺或者制造业,艺术更多的是针对人来做事情。那是不是说在这边,在某种程度上,越来越把艺术这个行业等同于其它的行业,就是人的味道越来越淡,更多的是看你怎么操作,你用什么手法,你的工具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而越来越不去问在这中间你的感受是什么,就这一部分东西特别特别弱,但往往这一部分才是最关键的,也是你做这件事情的原因,可能这是很大的一个区别,两个环境之间。
LM:这些会直接影响到创作方法。我有一部分作品强调一种过程,过程就是一种体验,所有的东西都是由体验得来的,而不是预先设定好的。你会看到咱们周围的这个环境,大多数的年轻艺术家,相对来说都过于讲求作品的结果,体验的过程是很短暂的。更多的是一个观念,去完成它。这样也不是问题,当大多数人都在这么做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里面就有问题了。它就会导致更多年轻艺术家的创作方式很单一。在纽约我遇到很多艺术家,并不是每个艺术家的作品都很好,他们的艺术结果都不是那么出跳,可是你会觉得每个人都有他所关注的东西,并且像做研究一样,用他的身体、知识、时间,一步一步的朝下做。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你会感受到人是沉浸在事物之中的,创作是快乐的。
LPY:我觉得这关系到一些创作类型的问题,就比如说有一部分的艺术家,他就是以自我的感知和情感来出发的,这种东西如果违背了他的感知的话,结果其实是放在第二位的;那有一些艺术家是从材料出发,他觉得材料是他的语言,他不带一些私人的情感,以具象化的方式呈现在作品里,有可能不是这么直接;还有一部分艺术家,是以这个体制为针对的目标,他是以刺痛或者搅动体制为他的工作目标的。我理解下来,这几种创作类型的区别导致他们的一些做法上,效果上,产生了一定的差异。
HY:这不是一个问题,在一个良性健康的环境里,你说的这些它都有,而且这个环境应该给予不同类型的每一个人平等的空间,去进行自己的创作。但是问题是,中国的环境是唯效果论的,你说的这些方式里,谁出跳,谁吸引了更多的眼球,吸引更多的讨论,我们就给谁空间,你会发现接下来所有的空间都做他的展览,这就无形当中助长了一种功利性。那个平等的环境没有了,但是这无形中引导艺术家往那个方向走,他本来做了一个自己的研究,挺好的,走自己的路,但是一急,或者他想要这个,想要那个,就完全破坏了他原来的节奏。你说的种类,都没有问题,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现象。
LM:种类不是问题,当我看到很多作品之后,我看到很多不同的艺术家,不同的艺术形式,我却发现有些东西是相同的,是不能改变的。艺术家必须要和他的研究对象建立关系,去靠近它,去研究它,要去体验它,这时候产生的东西就是有意思的东西,这些不是你想像中得来的东西。就像你要反对美术馆体制,如果你对美术馆体制并不了解,你对它没有体会,你的作品就不会有意思。不是说你对着它开一枪就是反对,或者炸一下就是反对,这些东西肯定是你想像的。
HY:五个月过去了,你又回到了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就是我刚才说的,环境其实没有变,你变了,又有新问题出现的接下来的阶段,你怎么来应对?因为你还要继续工作,我也不知道你的中长期的计划是什么,你是想继续留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还是说为离开做准备,或者直接就要离开?
LM:回来之后,我觉得我的工作的可能性很多,我在哪儿都可以工作。这也产生了我去农村工作的念头,这是因为我对环境没有了很大的依赖性。另外,我感觉到无论我在哪里,都有很大的工作空间等着我去做。我在说这个环境有问题的同时,我也在思考,我作为一个个体,在这个环境里面,从哪里插手,去做什么? 我去纽约之前我们刚刚开始做PDF杂志,那时候我觉得就当作我们学习、分享知识的一个工作。但是去了之后,再回看国内的情况,突然感到这本杂志的重要性。在这个环境里,它所起到的作用是很大的。意识到这一点,我就知道我还可以在这上面继续工作。我去年做过一个茶话会,观众是被邀请的,讲演者也是被邀请的,为了保证一个有效的交流,我意识到这个工作也很重要,我还可以继续做这样的工作。还有,针对我个人的创作,我想换到我的老家来创作,那是一个没有美术馆,没有画廊,没有策展人和艺术家的地方。我去农村是逃离上海吗?其实不是,我去农村的工作反过来是对上海这个环境的有益的补充和试验。
LPY:那你准备在农村呆多久?
LM:还不知道,看情况吧,我还没有开始行动,不会先给出什么承诺。
HY:那这个将要在你的家乡去开始的项目,是否会是你接下去的创作中一个比较长期的计划?
LM:不排除这个可能,但是对我自己来说,我不会去设定一个时间,他会束缚我。当我觉得需要离开的时候,我就会离开。对于艺术,不承担任何责任,因为当我承担责任的时候,它会给你我很多动力,同时,也会成为我的束缚。这也是艺术家与社会实践者之间存在的微妙差异,就像一首诗歌和一篇记叙文的差别一样,当我的实践和行动中失去了诗意或乐趣,这时就该离开了。具体是什么时候,要随着我的实践才会知道。
HY:继续刚才的话题,你提到在纽约的这段时间,你慢慢意识到PDF这份电子期刊在这个环境中的重要性,那从你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重要性体现在哪里呢?
LM:我看到了PDF与现在中国的很多艺术杂志不同,就像看到一位好的艺术家与一位投机商人之间的差别一样——好的艺术家,他的眼神是清澈的,是温暖的,投机者虽然是精明的,但是总有那么几分狡黠和势利。PDF对于我来说,就像一道淳朴率直的目光。正是这种不同,让我对PDF充满信心。
HY:月初我在时代美术馆的一场圆桌讨论中(《脚踏无地:变化中的策展》,2012年7月2日至4日,广东时代美术馆),介绍了PDF,其实大家也都比较关注,也提出了很多问题,比如PDF的内容从开始至今有没有什么变化;是不是会一直延续我们三个人编辑全部内容的方式;还有特别问到在PDF的初期,比如我在第一期中对时代美术馆邀请侯瀚如策划的展览所写的评论文章(《怀疑的力量》,胡昀,PDF01期),还有李牧撰写的对纽约新美术馆做的三年展的评论(《没被控制还是被控制了?》,李牧,PDF02期),对国内外正在发生的展览进行评论,但在之后的几期中,这种类型的评论少了。我在回答中提到从一开始做PDF,我们就决定至少开始的五至六期,是由我们三个人来编辑内容的,但之后不排除邀请其他人加入进来,为PDF提供内容。关于内容上的变化,我们之间从来不限定内容,对于展览或时事的评论也是顺其自然,这也是PDF的不同所在。关键问题是,你能够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提及很多问题,但这么做是不是当下这个环境最需要的?这个环境中个个都是明眼人,大家都很清楚你提出的这些问题,当然,把问题提出来是需要的,但是如果只是这样,根本不解决问题。而对于试图营造一个更长远的良性发展来说,通过这个电子刊物,能够提供一个至少在当下还无法去给出判定的可能性才是关键,真正客观的来看待所发生的事情,提供一种相对健康的,平和的态度。而这也是我们从03期开始的一个持续性的板块《对话》,我们直接与艺术家交谈,这也是与当下的环境直接有关的,与近几年开始的“年轻艺术家热潮”有关,这其实也是针对当下的环境,情形所做出的反应,所以在PDF这个平台上,我们更希望去建立的是一个可以延续的平等关系,而在《对话》这个板块中,我们也许在明年,或者后年,还找同样的艺术家再做一次对话,甚至问相同的问题。我也想了解一下你们对于PDF接下来发展的看法。
LPY:我也得到了一些对于PDF的反馈,很多读者比较感兴趣的是我们从自己作为艺术家来谈的感受,包括自己在创作中所碰到的问题,也有很多对PDF中的介绍部分感兴趣,因为国内的媒体对于国际上的很多艺术家个案或者展览还没有比较详细的介绍。我认为从自身出发去谈一些创作中自己面对的问题也是PDF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特点,而倾向这部分内容的读者可能就会对于介绍性的内容有意见,他们觉得自己从其他途径也可以了解到,而从我的角度来说,我也发现自己并不是特别适合去撰写一些介绍文章,可能也有语言上的障碍。所以之后邀请其他人参与进来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LM:但是我觉得,PDF永远都不要被外界左右。PDF不是为别人做的,如果我们提出的问题引发了一些同感,那固然不错,但我们选择一个真正让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才是关键,无论是创作感受,还是展览评论,甚至转载一篇别人的文章,这样才会有我们真实的情感和温度,和我们创作作品一样。不要去看别人需要什么,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在经营一个公司,而是在做一件我们喜欢的事儿。有意思的地方也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当我们对某个展览感兴趣时,我们会去写一篇评论,也可以去找一个感兴趣的人谈话,更可以发发憋在心里的牢骚。也许PDF还不是那么完整、成熟,但是确是丰富饱满的,有生命力的。
HY:那你觉得如果涉及到邀请其他人来提供内容,我们可以采取的方式是怎样的?或者要求是什么。
LM:就像你介绍一位艺术家的创作一样,你对于这个想要邀请的人要有兴趣。但千万不能策略性的去经营这个事情。
LPY:那这种兴趣是由我们之间的某一个人来决定吗?
LM:可以一个人决定,也可以三个人一起决定。
HY:但首先我们三个人应该互相告知,第一步应该是让我们三个人清楚邀请的理由,其实我们三个人对于PDF都有自己的判断,所以在邀请时,我们应该有基本的把握。
LM:但不能为了邀请而邀请。邀请别人来撰写文章与介绍一位感兴趣的艺术家一样,最终面对的都应该是我们自己,整个传递出的气息还是我们三个人。
LPY:那你觉得在前五期中,这种气息形成了吗?倾向性明确吗?
LM:我从来不去考虑这个。
HY:这个也不用考虑。或者说,不应该变成我们的束缚。
LM:当你刻意去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去试图规划,塑造。
HY:通过看PDF,能够看到我们三个人。
LM:对,在杂志的内容上也是这样,一期可以是50页,但也可以只有一篇文章,切勿进入惯性的模式。特别是当我们意识到存在某些重复的时候,会有一些自动的警觉,问问自己是否是真的感兴趣,还是为了填满内容。但从我个人而言,谈话的形式还是很不错的。
LPY:我想到大概是在准备第五期的时候,我和胡昀也沟通过,从内容上看好像都是艺术家的个案,是不是有点重复,也许我要去写一篇其他内容的文章,但现在看来,没有这个必要,不用像其他的艺术杂志一样,去分配内容。
HY:对,不要去考虑这个。因为我们做PDF的原因,就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在关注的东西,哪怕整期都是访谈也没问题,我们不是要做一期“访谈特辑”,而是恰好都在关注某位艺术家的创作。
LM:这也说明当你不去刻意的要求某些东西的时候,可能性反而变得很多。
HY:这种对于目的和方向的弱处理,也恰恰反映出PDF的时效性,因为我们所关注的东西一直在变化,而环境或多或少都会对我们产生影响,我们的选择必然与这些影响有关,所以我们每次做的谈话,甚至撰写或者转载的介绍,都是我们对于当下的反馈,所以这个本身是在发展的。
LM:像植物一样,是在生长的。
HY:我们并不是在铺开一个面,试图囊括全部,而是在延续一根线,哪怕是极其细微的。
LPY:与我们三个人自己的成长密切相关。
LM:对,会随着时间显现。
LM:平原,你下半年有什么计划?
LPY:可能最近一段时间都会把精力放在9月份的个展上。
LM:这个展览要探讨什么呢?
LPY:与我在PDF中的几篇文章有直接的关系,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些问题,而这一次的展览可能更多从感性的角度出发,也是我去年在瑞典的个展《胶囊》的一种延续,因为还是围绕一种中间状态展开。
LM:我还是想问你,这种一边工作,一边延续自己创作的忙碌状态,影响了你自己的创作,还是帮助了你的创作?
LPY:也许因为从一开始我就处于这种情况之中,所以我已经有了一种免疫能力,我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想自己的创作,什么时候要工作。
HY:那就是至少现在你没有感觉这种状态在干扰你。
LPY:对,因为我一毕业就在广告公司上班,也同时开始了自己的创作,所以也习惯了,对时间的安排也可以比较妥当。
LM:其实去年在瑞典的那段驻留的时间,可能你可以完全将精力放在自己的创作上。
HY:但是我觉得在那段时间我同样非常焦虑。
LM:是因为有很多时间?
HY:不是时间的多少,因为我也在那里呆了几天,去之前我觉得平原不用工作了,应该可以比较放松去进入状态,或者至少可以享受生活,可是去了一看,完全不是这样,他比在上海的时候更焦虑。
LPY:对,所以可能工作并不是导致我焦虑的原因,本来就是这样一个人。
LM:我不相信焦虑会是一个人的性格。
HY:这也许和平原一直关注的东西有关,你会对某些东西特别敏感,一些我不太会去注意的部分,而且这个环境对你的影响也很大,这是不可否认的。
LM: 在第四期的PDF中你写过一篇文章,“要选择一种什么角度的表达才能让我们安然入睡?”,文章中你列举了很多理由,但是都不够。
LPY: 对,我找了很多理由,很多都是我关注过的某一个艺术家的创作出发点,但好像在说仅仅这些理由都不够,有些人从感知出发,有些人从现代主义出发,有些人从消灭现代主义出发…… 我当时把我能想象到的出发点都列出来,说这些都是不够的,所以……
LM: 你真觉得这些都不够吗?
HY: 你所说的这些不够是因为它已经有了,你再这么做很难再超越它,是这种角度的不够,还是你真觉得不够?
LPY:好像是不满足 。
HY: 是你觉得无法满足你自己,还是无法满足环境?
LPY: 更多的是针对我自己吧,因为我也尝试过几种角度去想问题,但是好像都不属于我,还是这种作品里产生很多矛盾的方式更适合我。就是有点说不清楚的那种感觉……好像更适合。
LM: 我有点没听懂。
HY: 我听懂了,其实很明显就平原的创作,你可以看到最近三年,他方向很多,可以说每次他花心思做的作品,都在变,就像他的那篇文章一样,好像出发点都在变。就是你自己感觉是不是可以这样,可以那样,平原的意思就是这种也许就是他的一个方式。
LPY: 所以在你去纽约的前一天我去了你家,你也说到了这种状态,目前的现状就是这样的,希望他有很多个点,都是自然产生的,不去规定一个很明确的方向,我觉得这就是我现在。如果说你前面说的因为体制需要,去演一个“东西”其实也不难,但是我觉得不是我真实的状态。
LM: 去演?
HY: 就是类似我们也可以分析出“体制”好像需要什么样的东西,那去“演”一下,有个明确的形象之类的,其实也不难,但是他说没有那样去做。
LPY: 我觉得这个阶段就是在试,这也是不能回避的,必须要尝试完,什么时候会有个很集中的点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必须过了这个阶段。
LM:也许我跟你状态不太一样,我试过了很多方向了,我告诉自己,我要出发不需要任何理由,而你却是说,这个理由还不够,那个理由还不够,很多理由都要去尝试一下。哪个理由都可以,也可以不要任何理由。我突然想到电影里的一句话: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是哪个电影,周星驰的电影吗?
LPY: 好像很多电影里都有这句话。
HY: 但我觉得说这句话的人他有他的理由,所以他才会这样说。那你问他你为什么爱他,他会告诉你我爱他的性格,我爱他的……,就是爱。你一定要让他说的话他还是能说出一个理由,这也许是平原一直在找的一个东西。
LM: 还有,有时候我觉得很多阐释也好,讨论也好,都是多余的,这都是再给自己一个行动的理由,而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没什么可讲的。
LPY: 包括有时候当你做完一个作品,有人问你是怎么想的,你会突然放空,觉得没什么好说。
LM: 可是当我去和别人交流的时候,又能启发我很多思考,也能学习到很多东西,我是在这种矛盾之中。就像接下来在广州时代美术馆有一个展览,全部是讨论,就是一组又一组的艺术家讨论,我在想有什么好讨论的。那么既然去了就听听别人是怎么想的,但当你参与进去了打开话匣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别人和你的不同,包括知识的不同,以及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不同,这会激发我很多思考。
HY: 我也是有这个心情,我把他看成一个无意识的自我封闭,觉得没什么好说的。但是有时候想想为什么不呢?打开,也许还是不知道,有什么关系呢?也许能带给你新的东西,也许什么都没有。时刻在提醒自己,要有个更开放的心态。就像你说纽约的很多展览,你会用以往的经验去扫一遍,或者一个一个去读,有可能读完后发现真没什么意思,但你也没有损失什么,甚至于他会给你很多启发,你以后在处理这样问题的时候会怎么做。
LM: 我离开纽约的时候有一点小小的焦虑,我觉得这5个月我大多数时间都在晒太阳,在工作室里发呆,在河边散步,和朋友喝酒聊天,快要离开了才意识到很多地方还没去,很多人还没见, 很多展览我还没去看,就有一点焦虑。我过了几天就不焦虑了,我问自己:你以为你能把纽约的展览看完吗?累死你也看不完,更何况还有巴黎、柏林、伦敦……你做艺术不是为了看展览的,今天看展览是为了将来能少看展览。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释然了。
LPY: 你说你后来扫了唐人街,是扫了多久?
LM:一共用了7天时间,就是阶段性的扫,加起来正好7天,将近40条街道。
HY: 说说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是什么促使你做这些?
LM: 我喜欢那个地方,唐人街所形成的规模真的让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中文招牌、中国人的面孔、中国的餐馆……朋友们一约就是到唐人街吃饭,我剃头也到唐人街,买东西也到唐人街,所以站在那里就有种“自己的地盘”的感觉,可是当我看到背后的华尔街的高楼的时候,它又在提醒我,这不是我的地盘。然后呢,那里真的很脏,美国的其他街区,包括黑人的街区,都很干净,只有华埠是最脏的,地上很多垃圾和痰,特别脏,这个时候我会特别感慨,既喜欢这儿又特别恨这儿。再有一个,我到快离开了都没做什么作品,确实得考虑该做点什么,那做点什么呢?所以我就产生了扫唐人街的念头。
HY: 那你觉得这个是你的作品吗?是一个作品吗?
LM: 是,我会把它作为作品展示,所以我在做的时候就让另外一个人用摄像机记录。
HY: 那你觉得它是一个录像?
LM: 我只留下了录像记录。
HY: 我是指展示,作为一个作品展示,不会有文字?
LM: 我不希望有过多的文字说明,也许会说一下作品的背景,有利于别人了解这个东西,而且我比较感兴趣把我作品承载的物质简化到最低,不要把它复杂化。
HY:那边没有人负责这个街道吗?
LM: 唐人街也有清洁工。因为中国人的习惯太糟糕了,虱子多了不咬人, 他不会去维护它,也没法维护。很有意思的是扫到最后一天的时候我在地上扫到200美金,还有就是扫的时候遇见一个清洁工在前面扫,我就和他一起扫。
LPY: 那基本上你在那边生活的内容大概是?……晒太阳……
LM: 基本上是,下午之前吧,都是不太出门的,起的晚一点,起来之后吃早饭,收收邮件,在屋顶花园晒晒太阳,然后吃中饭,吃完之后考虑今天干什么。 骑自行车去附近转转,然后一下午就过去了。有时候骑车到河边上,觉得不错,一坐就俩小时……看着天黑了,然后骑自行车回来。我在那有一间工作室,在工作室里呆着我感觉很舒服,我提醒自己不要被工作室限制住,因为整个城市就是工作室。 其他的艺术家朋友经常会问我,你怎么老是不在工作室?我说我不是个工作室艺术家,所以我常常一个星期才来一次。
|
------------------------------------------------------------------------------------------------------------------
© iamlimu.org 201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